〔李解万象〕
张雷和张小雷
文/李炳亭

五百年前是一家的他俩本不认识。但彼此都与我熟悉。
我要借用一部电视剧的名字,来形容我和他俩各自的关系,“我的兄弟叫张雷”和“我的兄弟叫小雷”。他俩一个在江苏,一个在江西。他俩的学校一所叫“前景”,一所叫“宁达”。两个人的父亲都是教师出身。张雷的父亲文革挨批斗,临退休之前光荣地入了党,自己一高兴,就逼着全家人举杯庆祝,嘴里还大喊着,“醉表心声”。张小雷的父亲文革被遣返原籍,平反后却拒绝返城,自称看破红尘,常邀三二知己,吟诗作赋,飘逸如隐士,一辈子桃李满园。
张雷的父亲想让儿子安安稳稳地当老师,张小雷的父亲却反对儿子在教育局做干部。
两个人都选择了逃离教育,经了几年商,赚了一点钱,却都又不约而同地办学校,最终兜了一圈子,还不是再回教育了吗?人生真是有趣,谁也无法拎着自己的头发,跳出命运的手心。但张小雷偏不信命,就改了个名字挑战一把,从此张小雷变成了张项理了。
张雷曾经对崔其升说,您是我的大恩人,要是没有杜郎口,也没有“前景”的前景。“前景”在昆山,张雷说,那是典型的硬件很软,软件很硬。要不他凭什么和硬件很硬的公办学校竞争,更何况“前景”的学费不菲。张雷说,“前景”的竞争力就来自课堂这个软件。“把学生当人”,办一所“儿童自己的学校”。
“前景”学校有三个看点,一是他们的“拖课”,一个老师可以同时上四个班的课;二是他们的“去领导化”管理,学校不设中层,教师的工资由每个人自己定;三是他们出台了自己的学生学习法,教师权益法,看他们是如何“把人当人”的。
“前景”课改初期,曾给“共同体”惹过一个小乱子。说起来真是滑稽,他们曾经聘请的某位办学顾问,实名举报崔其升、李炳亭诈骗,有关单位如临大敌,派人找张雷录证词,张雷说,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我是法人、董事长,我被诈骗,我自己竟然不知道,你们查的到底是什么。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张雷气不过,我和崔校长反过头来都安慰他。这样的事情,我和崔校长这些年经历了不止一次。
磨砺多了,心反而静了。
搞课改,得“皮糙肉厚”,打不垮,捣不烂,做响当当、硬邦邦的“铜豌豆”。
人品是否经得起考验,才是人生最大的关口。
“前景”现在已发展成一个教育集团了,在校学生七八千人。我一直看重“前景”,“前景”每一天都在成长,是因为他们始终在路上追求生命里的“前景”,是因为他们永远具有的学习精神。
想起前景校石上的那四个大字,“前景光明”,红彤彤的耀眼夺目。
张项理当年因为搞课改,先后辞退了两位校长,他说,头撞南墙我也得搞课改,这个当兵出身的人,懂得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句话蕴含的哲理。
张项理有许多名言,教育要促进文明的进化,坚决不做“类人猿”那样的教育。把每一个问题学生当成生病的孩子。
课改是炸掉应试教育碉堡的炸药包。
宁达,这所当初被人称为“只捡破烂”的学校,一跃成为全国课改名校,有了“江南杜郎口”的美誉。
可惜的是,几年之后,他兴趣转移了 ,本不太长的脖子上挂一架伸头探脑的照相机,他迷上了摄影和旅游。
当我写这篇微信时,我不知道他此时正在哪个国家晃荡呢,兄弟,你在“他国”还好吗?我是多么盼望他重新回到课堂上,用他最擅长的隶书,饱蘸浓墨,再重新书写一幅“课改万岁”!
张项理和我同年同月生,足足大我四天。他偶尔会“教育”我说,怎么也比你多四天的见识吧,你大声叫“哥哥”。
怀念在庐山西海的月光底下,我和大我四天的“哥哥”一起散步。透明的月光洒在我们身上,像披着银色斗篷,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战士”,夜晚真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又像有谁在远方擂响了战鼓,让人听得入迷。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教学如何升级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教学如何升级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教师是谁?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教师是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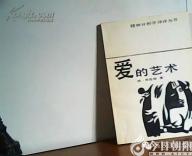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爱是人格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爱是人格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李炳亭课改答问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李炳亭课改答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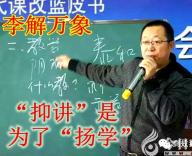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抑讲”是为了“扬学”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抑讲”是为了“扬学”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课改是一场通向未来的革命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课改是一场通向未来的革命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我所主张的“三合一”改革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我所主张的“三合一”改革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教育是一种“抉择”
【今日朝阳网 李解万象】教育是一种“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