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梦笔》(五十一)
——“印象、方向、影响与焦虑……”
文化信使/辽西雷子 编辑/雅贤
一、
冬天空旷的原野上总是飘着一层雾气,随着时间的不同,雾气的颜色轻重厚薄也不同。那个冬天的清早从老家出来,在路边拦了一辆车,车子启动后,慢慢驶过村庄,进入公路上开阔的地带,回头看,村庄渐渐被一层氤氲的青雾所掩盖,夹着早晨的炊烟……烟雾中母亲站在门边不舍与惦念的面孔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感觉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样变得依恋、依赖,而我在外读书时,母亲从来不送我,想着这些,眼里便开始潮湿……
山脚下的白雾越来越浓重,那是背对太阳的一面,清晨的阳光还未晒到。雾从山谷上升到山腰,便浮住了只横向流淌,而不再升高;一脉蓝色的山梁浮起于白色的雾气中,那些落叶的乔木树干黝黑,与常绿的松树一起在雾中隐隐约约。而山的另一边——向阳的一面,连那些黄的、白的、红的草都清清楚楚。此时想起莫奈的绘画,那些印象之作,传达的似乎就是这些雾气中的事物在光线下的变化。看到雾中金光的狮子,老虎斑斓的皮毛,安静的猫的胡须,松鼠伶俐而狡黠的眼睛……雾的变化,光线的变化,幻化出一个大千世界。一切那么真实,又那么虚无,在你似乎就要看清的一刻又什么都看不清。
那时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在一条弯曲幽深的狭谷中走着,一会儿柳暗花明,一会又山重水复。每天在低头的阅读与抬头的眺望中,喜悦、忧愁、困惑与迷惘交织在一起,连天气的阴晴月色的有无都能影响我,像一个发烧的人,亢奋着,又失落,冷漠着,这是阅读带来的焦虑。尼采、叔本华、弗洛依德、爱默生、博尔赫斯、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当这些大师一一步入我的视野,眼前似乎一片开阔,却又罩着一层又一层雾气,感觉自己快要被窒息了,在大师们的光环与阴影下,在这哲思与诗思的空间里,我贫瘠的想像竟追不上我的脚步,一个人开始迷失自己。那是一种彻骨的绝望。一座座峰巅,已矗立成不朽的巅峰,穷尽我们的一生,也无法攀登到顶部,更惶论超越。这时卢梭、歌德与康德开始走入我的视野,让我渐渐看清在理性的严谨与感性的激情间有着某种融会贯通,一种诗意的理性渐显清晰。焦虑像退潮之水开始一点点淡去。
二、
冬天午后的田野上总是笼着一层暖雾,雾气离地面一尺多高,形成一个悬浮的隔离带。这些雾气有时是桔黄色的,有时是蓝白色,有时又是紫色,看着就在眼前,当你走近,那雾好像又后退了,总与你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些远远近近的树木,村庄,河流就隐约在这层薄雾的背后。所谓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也不过如此。此时我望的是雾本身。雾在游走,变幻,雾中的事物看上去似乎随着雾气的变化而变化着,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呆在原地未动,变化的不过是雾气本身。而雾也不过是光中微尘的浮动与变化。而光依然为光,尘埃依然为尘埃。空气依然为空气。
最初很喜欢梵高的向日葵。那是一团燃烧的火。一颗跳动的心。后来接触他的画作多了,看出他笔下的变化与用色的不同,即便是同为描画向日葵,也是不同生长期不同色彩不同形状的向日葵,有一幅是刚收割的,成熟的籽盘与籽盘边缘的叶子一笔笔刻画清晰,泛着冷冽的绿光,那么真实可触,一点不像印象派之作,倒更像一种写实。梵高笔下的色彩都带着一种厚重,让人感觉沉甸甸的,而且以冷色调为主,用色大胆、狂野,呈现的是一种挣扎、焦灼、与隐隐的不安。即便是金黄的麦田,在让人感觉到平和的暖意的同时,也让人感觉到一种似乎血液就要凝固般的窒息;而那些星空、乌云、乌云下的旷野与道旁树,它们都在一种冷色的宁静中透出一种强烈隐忍着似乎马上就要爆发的冲动与混乱。当然他也有清新一些的画作,这样的画作往往在用色上有了水粉般的轻薄与透明,仿佛午后瞬间的迷醉恍惚与宁静,这样的时刻对梵高来说怕是不多的吧。在他笔下更多的是即将被自身焚毁的土地、麦田、星空与向日葵,连美丽的鸢尾花都带着一种即将烧焦的炭味。创作与性格命运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文森特·梵高身上体现得尤为强烈。割掉自己的耳朵如果说是不堪忍受病痛疯狂的折磨,倒不如说是迷恋死亡的提前演习。麦田中最后的一声枪响尤如群鸦散去,又如满天星星燃烧着坠毁。在他身上印象(后印象)、抽象、写实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融汇,他那看似疯狂的创作表现背后其实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清晰。
作为印象主义绘画精神领袖的莫奈,他笔下的用色要柔和得多,他着重体现的是光与色的变化,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段的光线下给人的感觉都是不同的,他不注重事物的塑形,而每一瞬间事物都得到了最本真的体现。他的画作尤其是是晚年的画作让人感觉惟美梦幻与安宁。可能我自己身上有更多与梵高的性格相似之处,所以读梵高让我感觉紧张分裂甚至一种忍不住毁灭的冲动与可怖。而读莫奈的感觉则完全不同。他对艺术的自我放任与执著中更有着一种超脱,不惟传统,不惟理念,坚持自己的艺术直觉,走自己的个性创作之路。如果说命运影响一个人的创作旅途,最终一个人的创作之路也会影响他的命运。从莫奈身上体现出一种比较完善的生命与创作的和谐,于他而言,影响不足为影响,焦虑更不足为焦虑。因为在他看似“模糊”的“印象”中一直有着自己清晰的方向。
三、
一种焦虑消失,又会涌上新的焦虑,犹如西西弗斯不得不反复推动的那块巨石。写作的难度永远存在,只要这个人不想总处于自己的重复惯性写作里。这种惯性重复主要包括语词的重复,涵义的重复,意象与意境的重复,手法技巧的重复等。如果说重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表意的可能,让自己思的轨迹变得更明确清晰结实有力,同时它也削弱了文本的涵义,造成阅读的疲劳甚至厌倦。因此,重复是必要的,却又是必须极力避免的。这就产生一种尴尬,真实的情况往往与此相悖反。如果回头检视一下会发现,一段时间内的重复,不同时段的重复一直在持续,仿佛时间那个“宿命式”的圆圈。我们努力作出的也只是对“圆”的大小及弹性作出变化,我们所有的努力并未摆脱掉这种带有“宿命性的重复”。
方向的存在也只是大致的,就像每个人都渴望走到罗马,此时的“罗马”已不是原初真实的那个,倒更像立在空中云雾里的纪念碑,它引领思的上升。(但有时我又怀疑这种“思”对写作的有用与否,艺术直觉与思有时相辅相呈,有时又会背道而行。)而途中总是充满曲折回旋,才让人一步步登上那虚幻中的阶梯。所谓终极抵达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罗马”本身就已是虚幻,永远在路上才是追求者的真实状态。这便注定了一种绝望,或说无望——永不能抵达。如果希望给人坚持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却多半无效。恰恰是无望让人清醒认知自己真实的状态和处境,“置之死地,而后生”,进而坦然面对,回到“人之为物”为物之一种的自然状态。还有什么比自然、自然的状态更可贵呢,这是原始的力量之所在。
傍晚的雾气又一次在田野的尽头浮起。田野的中央还是那棵孤独的百年老柳,在夏日里柔曼婆娑,舒展一层层绿烟;在冬天宁静沉潜,不动声色。有一天当我走近它,走到它的背后,才发现那上搂粗的树干的底部已空成一个大洞,看上去触目惊心。上百年的风雨,在它身上刻遍沧桑,而它依旧站立着,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着……那一刻,我眼中又浮满潮湿的雾气,这么多年经过的人与事在眼前一一浮起、沉落、又浮起,有如傍晚浓重雾气中的滔滔江河……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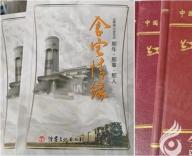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