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辽西雷子
想想,自己总是处于厌倦与灰暗的情绪中,难道这是因为对诗歌对文学对艺术的爱导致的吗?回答当然不是。让我绝望的不是写作,是生活本身。生活让人充满希望却又看不到任何希望。它让人活在绝望里。而恰恰是写作支撑了我的生命,或说延长了我的生命。
如果对诗歌的爱有时也会带给我绝望,那也是在诗写中对无法超越自己的绝望,而不是对诗的绝望。诗歌是美好的,一切艺术带给人的都应是美好的,它让人心向善。哪怕表达出的是绝望、灰暗、颓废与混乱,这也是因为写作让人在思考他的当下,是思考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至少他在看似喧嚣繁华的生活中不是盲目的、麻木的;他没有无知无识的沉溺于生活中。思考证明一个人作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着。这样看来,即便是颓废厌倦的情绪也是一种积极的情绪,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谁都没有理由因为这样一个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内心而指责吧。如果还是颓废厌倦灰暗,那么就把这一切进行到底,看看完全沉于黑暗的水底是什么感觉;之后又是什么感觉。
黑暗会一点点的打开,光是因为暗的对比才显示为光。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当一个人完全沉于暗的水底,此时的暗开始一点点变亮,那暗中的一切事物也会一点点变得清晰,如同它们呆在光亮中一样;而且比在光亮下看到的更柔和,更逼真。有如过滤了的记忆中的影像。这时黑暗不再是黑暗,恰恰是另一种光明。那么,一个人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沉沦就彻底沉沦一次。颓废就彻底颓废一次。只是不要轻易放弃挣扎和希望。别轻易被那黑溺死。
或许热爱文学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现世的荣耀。甚至不能给我们带来死后的名声。我们刻意追逐的永恒(如果有永恒),自己并不能看见,几十年的存在证明不了什么,那需要一个世纪甚至几个世纪的验证,才能被后来者所证明。但我们又何必在意这些,这些虚妄的名声与荣誉,它们真的值得人那么夸耀吗?这一生我热爱过了,为理想而追逐过了,这热爱与追逐本身(哪怕它充满了痛苦)就是意义。我们还要什么样的意义呢?难道只有功成名就,名满天下,锦衣而归才是人生的意义吗?却不知这些也仅仅是外在的形式,转瞬成空。日月穿梭,江河轮转,人的存在在整个自然中其实很渺小,那肉身的存在更是微不足道,如果这肉身于存在的过程中无所创造。只有灵魂是不朽的。
而诗歌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项锻造灵魂的手艺。是的,一项手艺。锻造灵魂。从存在的角度来讲,任何一项劳作都是手艺。一个农民,一个木匠,一个铁匠,一位科学家,一位哲学家,一位建筑师,一位画家,一位歌者,一个诗人,甚至一位僧侣,他们都怀揣着自己的手艺,从存在本身来讲他们并无高下之分。分别也只在一种手艺打造出的是可见的实物,另一种手艺研究的是虚物,是看不见却能感觉到的灵魂的物质。这也只能说明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并不一定非要高于生活本身。难道只有文学、绘画、音乐是艺术,农民精心培育出的一穗玉米,一个木匠一个铁匠精心雕刻精心打造出的器物就不是艺术?没有存在,就没有一切。
因此对那些文学艺术中的自戕者,我不认为是他(她)们死于自已所爱的艺术,是死于生活本身,是生活本身带来的绝望,而不是艺术带他们走向死亡。仔细看看那些自戕者的存在处境吧,生存带给了他们怎样的伤害。或许我自己经历过太多的灰暗与绝望,甚至想一次次走上与他们同样的旅途,但又恰恰是存在本身留住了我,让我反观着自己的存在,人的存在。如果他们那么多人的死还没有让我们看出死亡的虚无,我们真的需要再死上一次了。
不是燃烧,就是熄灭。你选择哪一个,除了你,没有人能做主。他人能带给我们的是一丝儿光,一滴儿水;也是一份温暖,一份希翼。或许它们能让一个绝望的人在黑暗中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或许只像吹过的风一样什么都不能让人抓住。因为更大的光只存在一个人的内心,除非他看不到自己内在的光亮。在生活中对许多事情我的表现或反应给人的感觉可能很脆弱迟钝甚至冷漠,但内心的我是强硬的敏感的是火热的。我自己经历体会过太多的伤害,所以看不得别人受伤,别人受伤,就是我在受伤。别人受难,如同我在受难。同时我也相信,除了自己,从来没有什么能打败自己。所以我看不起懦夫。如果你说你不怕死,那么你还怕生吗?生比死更要艰难,死只是一瞬,生却要漫长寂寞得多。自然的死亡帝王都无法避免,所以没必要为这样的逝去而过于伤悲。但一切的非自然消逝都是可恨而可鄙的。因为它带给亲人和友人的伤害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
我也依然相信诗歌与文学艺术最终带给人的是希望,美好,和内心的善。是最终的安慰和体悟了生命的智慧。不是绝望和死亡。而在追逐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却是必须的。不想再说了。累了。随你去。
2006-12-7晚烟隐庐
此时再想想,倒是自己过于执著“生死”、“有无”了。如果生与表达让一个人如此痛苦,死与消亡倒未尝不是一种解脱。我不会再如此“执”了。任何“执”都是愚妄而可笑的。
2006-12-8晨烟隐庐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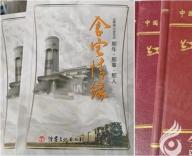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