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梦笔》(四十四)
“阅读中的异质及其它……”
文化信使/辽西雷子 编辑/雅贤
读《百年孤独》那本书,还是大学的时候,在图书馆排队,却总是被别人提前一步借走,很无聊,就去很少有人看的杂书里翻。常常是午后,阳光从窗子斜斜射进来,错落着照在那些书架上,很寂静,偶尔抬头会感觉很恍惚……后来终于等到了那本书。不过现在我已很少能记起那书和那些杂书里都写了些什么,只是记住了一些细节:从门槛底缝流到大街上的血,(那红,仿佛夕光下一条暗中奔涌不止又丝毫看不出奔涌的凝固之河;)一个呆在幽暗房间里摆弄些“小魔术”的人,(看不清他的面孔,也看不出年龄,只看到他侧影或背影的投入与专注;)突然刮起的怪风,(许多东西被风卷得无影无踪,好像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还有那个长猪尾巴的孩子和与他类似的先人(这样的人不是很长寿,就是活不太长;忽然想到小时候邻居家一个很正常的孩子,有一天忽然痴呆了,人们不叫他痴呆,叫他傻子,经常一个人在公路边走来走去,看见对面来人就傻傻地笑,捡地上的烟蒂抽……后来回老家,听说他失踪了;再后来,大半年之后吧,一个在山上牧羊的人发现悬崖缝里的尸骨,被风雨阳光腐蚀的破碎衣衫……从那衣衫人们辨出是他,那个傻孩子。)
有时我分不太清这些中哪些是现实里真实发生过的,哪些是阅读残留下的记忆。它们交织在一起,让陷入回想的时光也变得恍惚而不真实起来。它们也让我试图继续的表述陷入迷谷,开始我想说的不是这些,但时光走入了岔道,仿佛一枚铺展开的硕大的叶片,清晰的只是那些纵横的脉络经纬,脉络中是巨大的光的空白…
让人记住的不是那些常态,常态一直在身边,以至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忘不掉的是常态中的异质成分,平常中异样的表述。但又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试图说明的异质与独特之处读来让人感觉到异味,一种很不舒服的怪味豆,它让整体因这样的一个词或一个句子而变得“夹生”。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是与个人的写作习惯有关,技术处理失当;再是与有些人苛意追求奇异感的表述有关,这很致命;第三种便是和一个人的人性有关了。在这样的阅读中我几乎能看到或感觉到那个人写下那个词或那个句子时脸上怪异的表情和怪异的心态——此时的表述不是“异质”,而是“变质”了。很可惜。写作总避免不掉一时的个人情绪,(甚至有时就是在写那瞬间的情绪,)瞬间的变化,文字都会透露出来。这是一种瞬间的真实。如此,对个人情绪的超越与控制就越发显得可贵。这样说有点冠冕堂皇,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要超越“人性中的小”,它体现在瞬间的情绪表达上,你隐藏不了。如果超越不了这种“人性的小”,不管一个人怎样追求卓绝,都很难抵达卓绝之境。真实的心可以小的像针尖,容不得任何一点儿刺;但一转念,心又会变得海阔天空,风轻云淡。
今年买的杀蚊药和往年的不同,蚊蝇有没有药死倒没注意,自己却被药晕迷了三次,之后再不敢用了。如今那个高高的草绿色大药瓶还放在橱柜的顶端,其实早该扔掉的,但竟一直未仍。(有些东西放着,也许是经验的明证。就像一些无来由的痛,肯定不是没有来由的。我要直视它。而不是避开。)后来又闻到了一次这种药的气味,咳了好半天,但没有再晕倒,或许这就是抗药性吧。总有一天我会对它毫无感觉。有些东西抹去很容易。
女儿想吃香水梨,叫我和她去集市。很久不去市场了,乱糟糟的,看着很头疼。但女儿的央求不好违抗,只好穿鞋起身。来回不足1000米的路,竟几乎走不回,想想,很觉无味。秋风空自荡荡,惹人悲肠。观江河日浅,叹疲老之秋。
2006-9-20午间烟隐庐
附午前纸上戏谑的一个:
《三次。抽刀——》
第一次,长袖下手指微动
有风;
第二次,手指捏住
刀柄。
第三次,刀已入鞘;
无风。
存莫非老师改稿:
《抽刀》
第一次
长袖下手指微动
有光
第二次
手指捏住
刀柄
第三次
刀已入鞘
无风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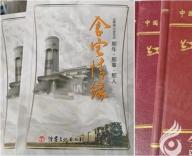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