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梦笔(二十六)
——“无聊间歇的碎语……”
辽西雷子
1、诗歌不是救赎之路。艺术让人陷入更深的孤独。梵·高、柯特·柯本、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特拉克尔、海子、三毛……哦,真好。“死亡让我们全都成为天使!”而无力死亡的人呢?或许自然是惟一的救赎。但这要等到我们的“老年”,才能在看开的同时放下一切。而这种老年心态的平静与豁达是否也意味着我们不再心怀热望?这时创作的艺术应是纯粹“以艺术为本”的艺术,而不再是“以人为本”的艺术。譬如博尔赫斯与卡夫卡肯定是不同的。
以艺术为本的艺术,它达到的可能已是艺术的至境,犹如武功中所说的人与剑合一,意念即是剑。这时萧杀之气往往隐去,艺术本身的“光”自主呈现。它带给人的是智慧和对生命真正的救赎。此时人已淡淡隐去,艺术凸显。而以人为本的艺术,它把人推到前面,呈现的是对人本身及人性的终极关注。这种切近的关注往往带着焦灼与烧毁的气味,它于人自身是一种摧残。而这更需要勇气。所以一些挚爱者会安度一生,另一些狂热者注定在生命的中途主动选择起身离去。
2、单纯追求诗歌之艺的惟美肯定是一条末路。自己的长处可能自己意识不到,但自己的缺陷自己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掩盖不足或扬长避短只是聪明者的捷径,而最终的诗艺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从自己的短处入手,或许正可以突破诗写的惯性及其所带来的阅读疲乏。诗艺更多的缘于一种自觉。
3、许多问题要综合起来看,把问题一个个掰开来争辩,或许会在单方面有所深入,但必然会造成整体的失衡。一谈到诗歌的“内容”和“技巧”,他们就争论哪个更重要,其实这种争论是多么没有意义。好的内容还要配好的技巧。所谓无技巧也不过是技巧用的巧妙,浑然天成。天衣无缝。
4、不要人为的把一个人雕刻成“魔鬼”或“天使”。我想所谓的“再神圣化”写作也肯定不是对人的“圣化”。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人,是人就会有人的一切欲望。只不过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我们有意无意中放纵或压抑了这些欲望。一切都是瞬间。瞬间的“我”是真实的。每个瞬间组合在一起的“我”又是相互矛盾的。世宾说“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赖。”这家伙,只这一句话,就让人喜欢他。
5、最近我一直在怀疑:宽容是不是最高的善。伊壁鸠鲁说快乐是最高的善,欲望的满足即快乐,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当然他的“欲望满足快乐说”并不是放荡者的快乐或享受者的快乐,它指的是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但我仍对他怀疑。灵魂的无纷扰或许可以通过时间的修炼达到,而身体无痛苦又岂是自己说了算?疾病折磨着多少天性快乐的人,你让他们抛开这真切的痛去体验虚妄的快乐,可能吗?我经常处于思考的沉重与写作的痛苦中,(此时身体的不适倒变得微不足道,)很少感觉到生命的快乐,那么我的善是什么?体现在哪里呢?难道我是恶的吗?有人说快乐也是生活,不快乐也是生活,那为什么不快乐地生活呢。对此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生活不是你的生活。
6、一位朋友说:“在辽西荒原的黑夜中,你的十字架上命中注定有三次受难:生存、流浪和爱情;同时,你的黄手帕上也必然写着三种幸福:诗歌、村庄和美丽。(——蓝桥)
生存不是单个人的生存,那么一个人的生存之难注定是思考并承受了更多人的生存之难。流浪,有的人在大地流浪,有的人注定要在自己内心的国土中流浪。爱情,一种无力抵达的完美,绝望与渴望间,成为一生的伤。诗歌,一种渴望飞翔的梦想;村庄,对古老故国家园的怀念;美丽,虚妄中创造出的不老的童话。是内心的苦难与幸福交织。
7、在莫非先生的花园里流览,看到先生的一句话:“要是一条路越走越亮那就完了。”其微妙处似乎不可言说,却让人意领神会。其实也可尝试着解释一下:譬如诗路,暗中的行走或许艰难,却也正是因了艰难而成为孕育力量的所在。当然这首先要求你是一个内心坚定的人,否则你很容易被这黑暗所摧毁。而贴近光亮的行走,由于可见而变得简单;疲乏、惯性与惰性也由此产生。这何尝不是诗写的末路呢。不光诗路,一切艺术之路皆是如此。伟大的艺术往往是在艰难中孕育和产生。看吧,“铁树在发芽。远处酢酱草在开花。”(先生题图语)
8、今年我窗台上的那盆竹节兰开得人触目惊心:那花瓣上的紫竟淌出了汁;血痂一般凝在纤细的花梗上。
9、疲乏者的白日梦。梦中的人儿蜷缩着,死亡一般,一动不动。而周边风起云涌;世界一刻也不曾安静。
10、站在那熟悉的篱笆墙外。看时间做了伪证。时间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对此,我无话可说。
11、脚丫开始一瓣一瓣地烂掉。什么药都不管用。父亲说过,扔掉鞋子,赤脚走走吧,什么病见土都会好。水泥地面有点儿凉;晒了一天的石板路很舒服;沙路上粗砺的石子硌得脚生疼。终于有土了。站在田野。泥土温热而暄软。天黑了。我不想再走了。
12、不知情的人看见了这一切,在大街上传说,这个女人疯了——竟赤脚穿街而过!
——疯就疯了吧。生命。还有什么好说。
2006-6-5日0:34分整理笔记 烟隐庐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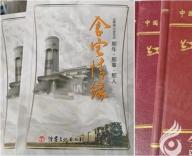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