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梦笔(十九)
——“表达;变得越来越艰难……”
辽西雷子
1、诗越写越恐惧;或者应该说是“畏惧”吧。和一位朋友谈起来,他也说到这种恐惧感:恐惧之一,是怕写完了拿出来,别人一下就看出诗的缺点;恐惧之二,是别人看了没感觉,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惯性写作,最终让读者都厌倦。而谁又有足够的能力摆脱这种沿习多年的惯性呢?生活一天天磨损着我们最初的激情与新鲜的感动,曾经令我们热爱的一切,如今都变得漠然。譬如爱情;我已有多年没在诗中提到这个字眼了,是不敢触碰,还是不愿触碰,自己都说不清……而那些最初的爱情诗笺,今天重读依旧令人伤怀到无言。
“真的:不是生存令人叹息
是我们自己过早丧失了相爱的能力”(——《窗上的手》雷子2001/9)
那过早丧失的,又岂只是“相爱的能力”;岁月如烟,而岁月并不完全如烟……那令我们淡漠视之的一切,原是最刻骨的伤痛和烙痕;一道道,在某一时刻,突然出现,清晰如昨。
2、表达;变得越来越艰难。一首诗完成,也是一段心路、一次经验的完成;它被扔在那里,等待它的是什么?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可以无限的相似并接近;但一颗心永远不会与另一颗心完全相同。那么一首诗的命运,只能是被误读,而且一再被误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阅历与经验解说着它,最终的可能是它离自己最初的简单的本质越来越远——或许,它因此而获得了被扩延的空间,变得更深邃;却也正因此,它被人为地疏离了自己的初衷……岁月也在篡改着我们的面孔,公然的;或是悄然不经意间。最初的无所畏惧变成了“慎于言”;对此,除了自我尴尬,是该欣慰,还是该悲哀?
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在自己看似坚硬的表象下变得越来越易碎,越来越不敢动;我碰到什么,什么就粉碎,那些透明的物质是多么易碎啊。玻璃、镜子,甚至不透明的瓷器、鱼化石,都在我不经意的触碰中跌得粉碎——满耳都是破碎的声音,在我体内不断发出回响……满目皆是碎片的闪光,这些光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剑,我无处躲藏;最终只能任由它们把自己一再划伤。手边的玻璃水杯又一次碎了,烟灰缸又一次碎了……算了,我已疲惫;我不会再在意它们是否精致优美,我要打造一只真正坚固的铁皮杯,盛放我自己——生命的烟灰。但,谁能保证,岁月的水渍不会让它也生锈,最后同样的归于尘土呢?
3、表达的艰难还因为:最初的诗写是秘密的;而现在它变成了敞开的。那些在纸上尽情抒写的岁月渐渐远了,当纸页卷起,一首诗也同时被卷起,如果不把它拿出来,它会永远成为自己的秘密。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秘密书写者的悲欢。当她走在人群中,她的面孔与周围的人没什么不同。她因此而走得无畏与坦然。但现在,面对网络和电脑,面对这更便利的工具,再重新退回笔与纸页的厮守,无疑是可笑的。面对这敞开,面对众多的质疑与责问,关切与担忧,一个人的自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坦然与无畏地表达个我真实的一切了。这是多么的矛盾啊。是刻意去掩饰,还是率性而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表达的两难。而我多么不愿面对一个虚假的自己。
或许,诗并不能承担什么吧。细究这生命的意义,原本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注定了一种必死的命运,谁能躲得过这场劫?为了让它变得有意味,我们学习,以丰富自己;我们恋爱,取悦别人,也取悦自己;我们哭,或者笑,或者吵,或者恨,或者爱,也只不过是为了让它不寂寞。我们本来就是在无意义中创造了意义的。在宇宙原初的虚无混沌中,上帝创造了世界,于是有了万物,有了人类,有了秩序;这一切也不过是“无中生有”——是“虚无的上帝”一场偶然的“寂寞无为”的产物。直到有了“社会”这个词,才跟着有了所谓的“道德”、“律令”、“责任”、“使命”、“承担”等等这些字眼——于是我们在自己制定的“律法”中套住了自己,几千年,再也不能脱身。我们都是自身的囚徒,呆在一个虚无的牢笼里;不同的只是有人欢喜,有人悲哀而已。
还给诗歌以本真的简单面目,它才会活出自己原初的生命力。别给它强加太多人为的“律令”与“责任”,或许它才能更有力地承担起自身所谓的“使命”。
2006-4-5凌晨3:16分烟隐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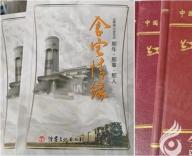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