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梦笔(十三):《诗学断想》(四)
辽西雷子
7、诗写的尴尬:在第3节“言说未尽的表达”中,我曾提到过理解与沟通的困难。对诗的误读与误解,一方面与诗写者本人有关,写者的经验与读者的经验存在着距离,付诸于文字,便暴露出文字表达的局限。而且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在一首诗中把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尽;虚实明隐,这就需要读者有一定的理解力和鉴赏力。有的人可能一生经历过无数的风波,所谓阅人阅世无数,但说到理解力,并不一定和这种经历成正比。理解力是需要一定的悟性的。就像有人读书读得多到“汗牛充栋”,却不及有人读几本书得来的智慧更多;有人一生修佛,却至死未能获得一点佛性,这是现实中常有的事情。记得诗人马永波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这种尴尬,他把几句因洞明世事而显平和旷达的诗句用手机发给几位朋友看,结果朋友们多以为他出了事,手机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询问,弄得他非常尴尬。类似的事情很多。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并不能很好地表达我们自己,诗写对严格要求自己的诗人们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写作方面来说,“写什么,怎么写”——永远是困扰每个作者的难题。也许有人会说,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这仅仅是写给自己看的,倒也不失为一种旷达与洒脱。问题是我们写了,还总想拿出来给别人看,希望别人与自己分享或交流;如此看来,你“写什么,怎么写”依然是一个避免不了的问题,单纯的分享也好,渴望交流也罢,你总得让人读了能感觉到你在表达什么或试图要表达什么。否则不是“对牛弹琴”,而是“牛弹琴”了——这是文字表达的悲哀。
既便“写什么”的问题你一时搞清了,而“怎么写”依然是时刻困扰我们的难题。这涉及到表达的形式和技巧。有人喜欢象征,有人喜欢隐喻;有人喜欢白描,有人喜欢写意;有人喜欢直接,有人喜欢迂回;有人喜欢叙述,也会有人一生只喜欢抒情;等等……所有这些形式和技巧,说穿了不过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手法,或者说是手段。(“手段”这个词多多少少暗含了一种“玩心机”之意,因此我并不喜欢用它;“手法”虽然也不乏“机巧”之心,但更多趋向于中性,但在表达上它又不如“手段”来得直接犀利。所以我还是选择用“手段”这个词。)一种手段用熟了,写的人会厌倦,读的人也会厌倦,这时我们开始想要新的尝试。但肯定也有人不,他可能一生都在一种风格模式里呼吸,所谓的“惯性写作”——这是表述的尴尬。写到最后虽然你还满怀热忱,而读者已不买你的帐了。
如果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那么这种“无技巧”中还是“有技巧”的,只是它已超越了单纯的形式与技巧,所谓浑然天成,天衣无缝。大师们的高明既在于此。
手艺娴熟之后,创新仍就不可避免。否则大师也会走向他孤单的末路;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很有成就的诗人最后写出的作品反不如他高峰时期的创作更吸引人的一个原因。诗写的尴尬也由此可见一斑。创新一方面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另一方面就是全部推倒后重建。原有基础上的创新因为根基稳固,而显得易于被接爱;但不足处是很容易裹足不前,与愿相违。而全面推倒后的重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你要变成另一个完全陌生的自己,一种不被认可与接纳的危险也就不可避免。而我们多半的时候是需要在这种危险中前行的。
近读清代李渔的《窥词管见》,其中一段说的深以为然,原文引录如下:“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词如此,诗亦如是。最难得的是于平常处求新,而非险怪中求新。
2006-3-4凌晨1:25烟隐庐
2006-3-4日11:05改于烟隐庐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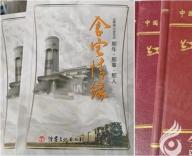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