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梦笔(十一):《诗学断想》(二)
辽西雷子
3、言说未尽的表达:理解与沟通的困难源于表达的困难;我们拚命的一再解释,却总是陷入新的误读与误解。这是很令人绝望的。就像我在诗文中一再表述的对死亡与黑暗的迷恋,其实是对未知事物的迷恋。说穿了,生命同样是未知的,它何尝不也令人迷恋呢;而对死亡与黑暗的迷恋可以看成是对生命迷恋的延伸。没有死,何来生;没有黑,又怎么会注意到光的存在。无中生有,有中思无,在无中感受万物的生成与化解,在有中体察无的无边无际;看似荒谬,实则是悖反中的同一。死生同体,光暗同体,有无同体;那么死是无,暗是无,生是有,光是有。生死有无,就此成为一切思考与写作的永恒的母题。天空一无所有,为何能给我们安慰?!泪水与内心的忧伤和愉悦交织;除了静静感受,还是什么都不说吧……
4、漂泊与还乡:少小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四处漂泊,浪迹异国他乡;年长后却一日日越发思恋还乡,而还乡后又一再地感觉陌生与失望……出走与回归,就此成为现代人永远两难中徘徊不已又挥之不去的宿命。漂泊是源于对自由的向往,而还乡更多已是一种精神上的还乡,此时它与地理上的地域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而人类精神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在一个神性和信仰迷失的年代,这种无根的孤独痛苦与迷惘已成为困扰我们的精神疾病,这在哲学诗人荷尔德林的身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因此他的“还乡之旅”也越发显得悲壮。
……阿尔卑斯山峦鬼斧神工,
那是远古传说中天使的城寨,
但何处是人类
莫测高深的归宿? ——荷尔德林《莱茵颂》
只要良善、纯真尚与人心同在,
人便会欣喜地
用神性度测自身。
神莫测而不可知?
神如苍天彰明较著?
我宁可信奉后者。
神本是人之尺规。
劬劳功烈,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荷尔德林
中年就患上精神病的荷尔德林,在时人所不理解的痛苦中已沉入他自己的精神归乡之旅,这种病使他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纷扰,更深地沉入一个人的纯净的神灵之乡。如此看来,他那被世人视作可怜悯悲悯的痛苦,又何尝不是他的幸福呢。他已返回了人类诗意栖居的处所,而我们还在这样的还乡路上一再彷徨……
5、神性写作与人性写作:我更愿相信人是有神性的。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阅读与写作时,是离神性最近的时刻;此时身外的现实仿佛并不存在,我们在黑中看到了自身的光……世人所歌颂的神灵悄然隐退,我们藉此却目睹了自身的神灵。这种神性写作,与世人所能理解的现实由于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精神的距离,而不被众人所认可,被视为虚妄;但总会有一些同样的人,他们能彼此理解与息息相通。这也是为什么已消亡的古人或异国人的作品,能超越时空被我们所理解并接纳的一个原因。这种“神性的写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灵的抒写”,一是“魔的抒写”;这在但丁的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天堂”之行与“地狱”之旅。而这种神性的根基依然是“人间”。没有人间的一切,天堂不成为天堂,地狱也不成为地狱了。当然,这种神性的抒写不止于这两个方面,它在每个人心中激起的圣洁的浪花是缤纷多彩的,也是深浅不一的。总的来说,它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的精神的关怀。
而人性写作更多体现了人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本体与现实的关怀。这种关怀因为切近人的本性而更易于被理解与接受。人性中的善与恶此消彼长,很难说清到底哪个是最初的根源;而从有无的角度来思考,无恶无善,那么善恶也是一体的,断然说一个人(或人性)的好与坏,是失之客观公允的,也是没有评判标准的,所谓标准也只是个人自定义的标准。几千年文化堆积成的标准也只是人类欲望下制定的标准,不是大自然的标准。因此一些人的“反传统,反历史,反理性,反道德……”就变得可以理解了,而理解不一定就是全部接纳。在这种逆反中,人性(包括善,也包括恶)得以更好地彰显;由此引发人更深入地思考人本身的存在和意义,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2006-2-27日16:00烟隐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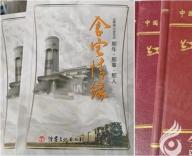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