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集文,男,1946年生于湖南邵阳,1965年参军入伍,即赴援越抗美前线,历经生死考验,在火线上入党。1967年凯旋归国,长期在部队团、师机关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攻读文秘专业,沈阳大学毕业。自悟丹青,成为湖南省美协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中国湖南湖山书画院执行院长,齐白石大师再传弟子。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新闻、诗歌、小说、书画及摄影作品1000多件。出版的专著有《邓集文画集》、《邓集文作品集》、《土气·豪气·文气》(花鸟画艺术家邓集文作品)、《风雨情》(邓集文诗集)、《多迈了一步》等多部。迄今,先后在辽宁、湖南、山东、浙江、台湾和香港举办个展和联展。2011年12月,国画《横行不霸道》荣登世界艺术殿堂巴黎卢浮宫,获法国国家美协颁发的“特别奖”。
邓集文转业后,一直工作在辽宁朝阳。豁达豪放、重情重义的邓集文把朝阳视为第二故乡,凭借其聪明才智在这里成家立业、成人达己。自今日起,《今日朝阳网》将陆续刊出邓老先生的专著《多迈了一步》(该书成稿于1982年,2015年初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步推介邓老的一些美术作品,以飨天下网友
多迈了一步
第十一章 身世

如同学生入学毕业,部队的退老补新年年进行。入冬,征兵工作开始了。
这次征兵地点:湖南邵阳地区。组织上考虑,王向东是已婚干部,在当战士期间只回过一次家,提干才半年还没安排休假,趁征兵的机会,让他再回去一次,也是组织上关心干部的生活。王向东心想:汤副政委说的,要在部队有大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实践,自己还没接过一次兵,去实践一次也是必要的!正好目前是副职,将来担任了正职,连队工作就脱不开了!因此他便高高兴兴地接受了组织的这次安排。
王向东在这次征兵工作中,与家乡公社副书记姜猛子一家产生了纠葛。在叙述这一纠葛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之前,需要先交代王向东的身世———
在湖南湘乡县有个名叫李家塘的地方,住着一个国民党还乡军官,有钱有势,威震一方。这人原名李富廷,本性凶狠,在战场上凶猛残忍,多次立功,上级赏名李虎腾。意在军界有龙腾虎跃飞黄腾达之势,然可悲,与上司为争一名妓女动怒,斗败气馁,解甲还乡。依仗在军伍里积下来的肥块,买田雇工,过起乡下财主生活来。
1946年初冬的一天,一位面颊消瘦的中年妇女从他的大院子里慌慌张张地奔跑出来,跑到大约相隔两里路远的一座低矮的茅屋门口,上气不接下气: “二奶奶呀,可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婶子、婶子,出了么子事啦?啊……”这是晌饭时候,茅屋里的老年妇女刚喝下一碗粥,碗筷还在手里。
“不得了啦,可不得了啦!……”中年妇女在门口,一手扶住门框,失魂落魄地重重复复地喊着。
“婶子,邓婶子,你、你慢慢讲,到底出了么子事啦,啊?别、别急……”老年妇女颤颤抖抖,忘了放下手里的饭碗,扑向
中年妇女———李虎腾的奶妈子。
“二奶奶您快去呀,成,成德老弟……李家用禾桶把他罩起来啦!何得了哦……”
成德姓王,是老年妇女的独子,在李虎腾家当长工。老人一听事关成德儿子,脑海深处 “轰”的一声炸雷,手中的碗 “叭喳”掉落地上摔碎了。 “他、他,他闯下了么子祸啦?……”老骨架子筛起糠来了。
“成,成德他犁田回来,赶牛进栏,虎腾他三房上茅厕,打身边过,跟成德答了句话,老不死的看见了,就说跟他三房有,有往来……”
“我的天啦,怎么得了哦!……”老人眼前一黑,双腿一软,融蜡似的就地坐下去了。
“二奶奶,先,先别烦,快,快去吧,我搀着您,去求求情,兴许……”
老人在邓妈妈的搀扶下,趔趔趄趄,一脚高一脚低,踏到李家大院里来了。
“虎腾老爷,虎腾老爷,您大恩大德,求求您……”王奶奶拜倒在李虎腾脚下。
“哼,你个臭老婆子,还有脸来求情哩!”李彪腾睁着一双牛睾丸一般大的眼珠子,脸上颤动着胖嘟嘟的肉, “妈那个匹,养的什么小杂种,长了几个脑袋,竟敢偷我的油……”
“老爷,老爷,您大恩大德,大恩大德……”
“什么大恩大德。”李虎腾怒色不改。 “想要小杂种啊,明日上区公所要去!……来人啦,把这个老婆子给我拖出去!”
这真是屋漏偏遇暴风雨,家贫又遭连天火。二奶奶回到破茅草棚里,与儿媳、女儿相抱痛哭,哭得昏厥命危。
眼泪和哭声在王家老少、三个女人中持续了三天三夜之后,邓奶奶又来了。
“二奶奶,虎腾他说,看在你家祖辈几代是李家的老帮工份上,成德可以不送区公所,但不要他再干了,让秀梅去顶替。”
“叫秀梅去顶替?!……”老人若被黄蜂蜇了一口,李虎腾坏,一向作践妇女,远近哪个不知!她苦痛地计量一下,花白的脑袋直摇摆:“不,不能把孩子往虎口里送!……”
“二奶奶,救成德老弟要紧,秀梅去了,有我在,您老放心是了……”
“娘,我去,哥哥都罩了三天啦!”姑娘悲伤地抽泣着, “白天我在他家干活,晚上我回来……”
为了哥哥,长得标致的十八岁的秀梅走进了李家大院。半个月平安无事。
但这是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半月后,李家添做新衣裳。这天秀梅一个人在客房里做了一会儿针线活,看看窗外天色已不大亮了,起身回家去,这时候,肥猪似的李虎腾,满脸堆笑,挺着大肚子,踏进门来。
“秀梅,你的针线活怎么样啊,拿过来我瞧瞧。”
“我不会做。”秀梅冷冷地回答,随手递过一件做成的衣服。
“嘿嘿,手艺还蛮不错嘛!嘿嘿嘿……”李虎腾的一双贼眼珠并没有看新衣裳,而把秀梅上下打量。
秀梅低着头,退后几步。
“昨天我告诉了裁缝,叫给你也裁一件,给你没有哇?你做上了没有哇?”
“我不要衣服,我要工钱。”
“嗨嗨,送给你的,送给你的,不扣工钱。”李虎腾慷慨其词,“你在我家做事,又是不小的姑娘啦,穿得破破烂烂的,客人们来来往往,不也丢我的面子嘛!”
秀梅低头不语。
“唉,秀梅,你晚上一个人回家,天黑,路上不害怕吗?”
“哥哥接我。”
“噢,那……哎。今天晚上赶紧做做你自己那件衣裳,住下别回去啦,啊!”
兔子跳进了秀梅怀里,“扑通扑通”直蹦。眼见事情不好,秀梅起身就往门口走。
李虎腾敏捷地退后一步,反手将门一带,然后背往门上一靠。厚肿的橘皮脸上堆起了狰狞的笑。一双贼眼球眯缝着,得意、贪婪地直盯着秀梅,就好比蜘蛛盯着撞在丝网上的虫子,山鹰盯着奔跑在秃山上的小兔。
虫子要挣脱丝网,小兔要逃离鹰爪。秀梅先是惊悸地退后一步,马上又猛劲冲了上去。她本想尽全身力气一下子推开这可恶的东西,冲出门去,可是有一百七八十斤的一堆肉,十八岁的瘦弱的女孩子哪里推得动!她反被他一把拽住,顺势抱住了。
“哎唷!”
屋子里传出一声苦痛的嚎叫。
“老爷,出么子事啦!虎老爷……”邓奶妈一路扯开嗓门惊叫,奔过来推开了客房的门。
“学狗咬人!”李虎腾左手捂着右手背,狠狠地瞪秀梅一眼,
“哼,你哥玷我的,没那么便宜!”说完愤愤地离开了。秀梅风也似的奔回茅草棚里,一头扎在母亲怀里,号啕大哭,悲伤欲绝。
成德的脸气青了,眼珠冒火了,在地上狠狠地跺了两脚,到柴禾堂里抓起一把砍柴刀,拔腿就要往门外奔。
“成德、成德,你,你……你疯啦!”老人推开女儿,扑上去拽住了儿子。
“李虎腾啦,我筪你的娘啊!你冤枉我,禾桶罩我三天三夜,原来是这么个鬼圈套!”成德铁一般的身躯扭动一下,“娘,别拖着我,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了,今天我豁出四两命来,非叫他的脑袋在地上滚西瓜不可!”
“成德,儿呀,闯不得,闯不得……灭门之祸呀!”老人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你看在老娘的分上,看在更莲的分上,她快、快落月啦……”
“嗨!”成德更使劲地朝地上跺一脚,好在地层厚,薄的话,这一脚也给跺漏了, “那,那只好走这一步了!秀梅,走,跟哥走!”
“上哪去?”老母、妻、妹一齐用惊疑的目光发着问话。
“上张家!”
秀梅自小跟张家的一位表哥订了亲的,一家都明白了。事急燃眉,只得当机立断。
秀梅跟着哥哥到了张家,与穷苦的表哥当即拜了天地。
半夜时刻,成德如卸重担,走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一程,又有了新的思考:妹妹,李虎腾得不到手了,可这比饿虎还狠的家伙哪能放过自己?!成德,你在这个地方待不得啦!听说外边世界已经乱了,到处都在打仗,穷人抱团闹翻身,开老财的仓,分老财的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眼下惹不起你姓李的,老子走,押粮去!
他回到茅草棚里,老母、妻子还在唏嘘。亲人声声悲泪就似把把尖刀刺痛着他的心: “我怎么能够丢开她们独自出走呢?我走了,她们靠谁生活?不是等着饿死吗?我怎么能忍……不,我不能走,我不能没有良心!明天李虎腾抓我去杀了,也算尽到了
我的一份忠孝!……”矛盾、忧愁、痛苦、怒火,一齐在他胸中升到了最高点,他站不定,坐不住,不断地咬牙、跺脚、叹气……
妻子虽在悲切中,但她从丈夫极度焦躁不安的神态中窥见了丈夫苦痛为难的心情,她走近婆婆面前,身子一沉,双膝跪地,声泪相混道:“娘,让成德走吧,李虎腾饶不了他!……”
“娘,我不走,活是一家,死埋一坑……”成德也跪倒在老人面前。
李虎腾饶不了成德,儿子留下来没有活路,有过风霜经历的王奶奶何尝想不到!但老人心中为难:媳妇已有好几个月的身孕,让儿子出走的话又如何吐得出口!然而媳妇突然跪倒在面前,她哪里还止得住老泪纵横,将媳妇一把搂在怀里: “媳妇,我的好儿媳……”
媳妇有孕在身,不能过于悲伤,婆婆扶儿媳起来,送进房里,劝慰在床上躺下将息。
过了一会儿,母亲出来了。成德走进房里,走近妻子身边。妻子从床上坐起来。他伸出叠茧粗糙的手掌,替她枯黄的脸上揩去泪珠,然后拉过她一只手,一只枯若鸡爪的手,用自己的双手捧着:“更莲,你来我家两年,你受苦啦,我对不起你……”刚强的硬汉子话到此处,喉咙哽塞了,豆大的泪珠纷纷滴落,滴落在妻子的手上、衣袖上。
“同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何谈对得起对不起呢?现在世道在变,我们都还年轻,说不定还有好日子在后头……”
“我这出去,要是有个出头的日子,绝不忘了你们!等着吧,莲……”
她抽出丈夫握住的手,身子挪动一下,下床来,揭开床头边几代人用过的一个木箱的盖子,从里边找出几件丈夫的破旧衣服,卷成个小包。
成德在自己身上摸索了一阵,摸出了几个铜钱,数了一下,一共七个。再摸,再也摸不出来了。他拉过她的手,把七个铜钱慢慢地、沉重地放到她的手心上:“这是仅有的七个……”
“你带着吧,出了门,身无半文怎么行?家里,总好对付……”七个铜钱仍放回了丈夫的手里。
家中清苦的程度,成德何尝不知,妻子说 “总好对付”,实际上又何对付?自己走后,家中肯定会揭不开锅……饿死她,是我的罪啊!不,我应该说给她一句话!这句话,简直是摘他的心肝一样令他痛苦的话,然而为了她,再痛苦也要说!他走近妻子,话未开口,泪珠先下。她理解丈夫过于沉痛,她深情地看着他,没有催问。
过了一阵,话,终于吐出口来了: “莲,我走啦,家里日子要是,要是实在过不下去了,那你,你就自己走吧,寻条活路……”
“饿死我也跟着娘,我等、等、等你回来……”她扑向他。他抱住她,紧紧地抱住她。双方都在抽泣,身子都在颤动,互相感染,愈是悲恸……
时候不早了,该走了!
在门口,成德左手拉着老母,右手拉着妻子,辞行道:“娘,更莲,我走啦,你们不要惦记我,有机会我就捎信回来,你们自个———多保重———”他慢慢地松开了手,转过身去,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
“成德,你,你回来……”
听到妻子的呼唤,他又折转身来。
“你给孩子起个名……”
穷人望东方,盼天亮!未来的爸爸沉思了片刻,说道: “就叫向东吧!不管是男是女,都……”
“王向东。”万分悲伤中的更莲轻轻地重复一句丈夫为未来的孩子起的名字,不由心中升起一丝的喜悦。
成德再次转过脸去,踏入了黎明前的黑暗,步子越走越快,走向了远方。
秀梅出嫁,成德出走,李虎腾苦心安排的阴谋落空,反而丢了个长工,心里好不窝火,急忙派出狗腿子,四处追捕成德。
捕了十天半个月,人影子也没有捕着。狡猾的狗腿子为了在主子面前交差,就谎说在哪里哪里抓到打死了,尸首抛到河里喂鱼了。
王家婆媳不明真假,担惊骇怕,日夜啼哭,在极度悲伤中,媳妇落月了,长工的后代———小向东来到了人世间。
贫寒加悲伤,年轻的母亲在月子里落下了病。
当时,一口稀粥都难得到口,哪还有钱来求医。病情急剧恶化,更莲自己明白,这个月子是过不去了,她想不清,穷人的命怎么这般苦!悲伤的泪珠在憔悴的脸上流淌,就似雨水流淌在黄土坡上。
“更莲,更莲,听娘的话,在月子里太悲了要不得,你别急,我去求求情去,弄点药回来……”老人劝慰媳妇,可是自己的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
“别—费—心—啦,八—字—命—里—注—定,我—死—啦,王—家—这—根—独—苗—苗,全—托—您—老—人—家—啦……”躺在草铺上的更莲,说话一字一喘息了。
媳妇在出满月的前三天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才过五十岁的王奶奶,看上去已是七老八十了,她把王家的独根苗苗———未满月的小孙孙搂在怀里,眼神发直,呆滞地坐着,就如同一株枯朽的老树,怀里小孙孙则好像是这株朽树上的一枝嫩芽。依着女儿的微薄接济,想着儿媳的嘱托,王奶奶坚持活了下来,在死亡线上挣扎着。老人成天满脸泪痕熬米汤,煮稀粥,精心抚育着王家的独根苗苗。夜晚,孙子饿了,没命地哭。奶奶哄不住,把干瘪的奶头塞到孙孙嘴里,孙子使劲地吸吮一阵,吸不出汁来,松开奶头又没命的哭。孙孙一声哭,就似割下奶奶身上的一块肉,奶奶心痛悲伤,枕边的一小块稻草总是潮湿着。
王家已到了如此地步,李虎腾还不死心。一天,好心的邓奶奶又惊恐万状地来到王家的茅草棚里。
“二奶奶呀,人说李虎腾心比老鸦还要黑,手比蜈蚣还要毒,真是半句不假呀!他恨你家现在没人为他帮工了,你家欠的债看来是没法还了。看着王家还有一根秧,好比鱼刺在他喉……二奶奶呀,李虎腾是虎是狼,要提防他下毒手啊!”
洪汹奔高坡,火猛投江河。为了王家不绝根种,王奶奶用草绳做背带,把孙孙捆在背上,一手挎竹篮,一手拄竹竿,离乡背井,漂泊他乡去了。饿了,东家求口剩饭,西家讨碗残汤;困了,这家庙宇里一晚,那个寺院里一宿。多少回挨了富人的脚踢棍打,痛不欲生,多少回被有钱人家恶狗撕拖,恨不能死……
1949年春天,瘦骨嶙峋的老人领着三岁的孙孙来到了邵阳地区的一个姜家院子。就在这一年,平地一声春雷,湖南解放了。
婆孙就此落下脚来,分房分田,翻身过上了人过的日子。
燃烧了多年的战火在神州大地熄灭了。接连不断地从部队上回来一些人,远近各村都有,每回来一个复员军人,王奶奶就去打听,见没见着自己的成德儿子?打听了一年多,毫无结果,老人失望了。
1951年秋天,邻居姜大伯的儿子姜猛子从部队回来了。王奶奶因为灰心,这回没有立即去打听。好奇的小向东跑到姜猛子身边,大胆地叫叔叔。
“哎,小弟弟,你号么子名字啊?”姜猛子弯腰伸手抚摸着向东的小脑袋。
他仰起头来,睁着一双大眼睛:“我叫向东。”
仰起的小脸蛋立即吸住了姜猛子的目光,他蹲下去,一只手托起向东的小下巴,惊疑地仔细地端详着这张小脸蛋,心里涌起了激动的回忆、猜测、不由自主地叫出了声: “像,像,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你说他像谁呀,啊?”老父亲笑呵呵地插问一句。
“唉,爹,这孩子是谁家的?”他转脸看着老人。
“你问他呀,远处来的,说你也不晓得。”老人哀叹一声,慢吞吞道: “是个苦命的孩子啊,落地二十七天没了娘,爹跟你一样,也走出去押粮了,是他奶奶……”
“他爹也当兵?叫什么名字啊?”莫非真的巧遇?!姜猛子愈加惊喜,胸中怦怦发响了。
“自打前年解放,老人家一直在打听儿子的音讯,远近打听了个遍,也没打听着。说是叫,叫成德,你在外边这么些年,碰没碰见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啊?”
“老家是湘乡李家塘的,是不是?”
“是呀,是呀,你见着啦?”
“嘿!我们是战友,一直在一起。”
“哎呀呀,这么巧啊,那快快快,向东哩?”激动的泪花模糊了老人的眼睛,向东就在他跟前也认不出来了,“快领叔叔回家,给奶奶报喜讯去……”
姜猛子伸臂抱起小向东,跨出家门去了: “往哪边走,给叔叔指路……”
“奶奶,奶奶,姜叔叔见到过我爸爸。”没进门,小向东就连声尖叫。
“!,么子,讲么子?……”老人闻声慌忙迎到门口,和姜猛子撞个满怀。
姜猛子顺手扶起老人,激动得浑身颤颤抖抖,热泪在眼眶里转:“大娘,我离开部队先到您的老家,听村上人说,我以为您老人家真的……没想到,您老人家来到了我家门口……”
也不知道是如何坐下的,就似久别重逢的亲人,姜猛子和王奶奶开始了欢欢欣欣地、亲亲切切地交谈。
“唉,猛子,那我成德儿现在在哪儿?”唠扯了好大一阵子,老人才记起这句核心的问话。 144
“他现在,他他……”姜猛子心里一缩,嗫嚅着答:“他留在部队上啦!”
……
连日来,五十好几的老人欢快得像个小姑娘,在姜家转个不停,一会儿让姜猛子替她写封信,一会儿说要给儿子寄东西。老人越是欢快喜庆,姜猛子越加愁烦不安。若将真情相告,老人又何受得住?!然而不说又怎么行?婴儿在怀,总要分娩!第五天,姜猛子怀着难忍的苦痛和恐慌,来到王奶奶家,拉着老人的手,颤魏巍道:“大娘,从今以后我就是您,您的儿子……”
老人骤然一惊,险些昏倒。“我的成德儿,他他他……”
“大娘、大娘,您老切莫悲伤,听我讲。”姜猛子立即扶住老人,“成德跟我前后只差三天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编在一个班里,我们俩特别合得来,亲哥俩一样,打起仗来彼此关照,互替生死。有一回,我们的子弹打光了,一起被敌人捉住。当天晚上,我俩互相掩护又逃脱了……”
王奶奶小声的抽泣着,惊恐地倾听着。
“前年五月,我们参加了攻打上海的战斗,反动派垂死挣扎,城防工事一层又一层,敌人躲在碉堡里架机枪扫射,我们队伍推进很艰难,好多同志被机枪打倒了,成德红了眼,抱起一根爆破筒冲上去炸碉堡,没等他接近,他也被打倒了。我跑过去接替
他,见他身上伤了好几处,他没有多少力气说话了,他一字一歇地说: ‘猛子,我怕不行了,我只有一件事托你,等仗打完了,全国解放了,你有机会回家,代我探望亲人,老家在湘乡李家塘,家有老母、妻子,还有一个孩子……’我流着眼泪向他点
头,我从他手里拿过爆破筒冲上去了,担架将他抬下火线去。战斗结束后,我急忙寻找他,到处打听,哪里也没有找到……”
老人止住了抽泣,揩干了泪珠,直挺挺地坐着,不言语。看得出,这是老人受了儿子英雄精神的教育、感动、鼓舞……
“大娘,往后我猛子就是您的成德,您老的晚年生活、向东的抚养念书,不管什么事,有共产党,有人民政府,有我,您老人家一千个放心……”
姜猛子的证明, “烈属光荣”的牌子挂上了王家门头。姜猛子凭着出身苦,复员军人,立过战功,共产党员,本人年富力强,很快被群众推选为党的领导人和村干部。王奶奶婆孙受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优待照顾,更添上姜猛子各方面的周到关照,老人过着幸福的晚年,小孙孙茁壮成长。烈士子弟在政治上的吃香,骄傲与自豪便自小与王向东结伴。在成长过程中,岁月自然陶冶了他一些独特的习性:一是喜欢当头头。在入学前的幼童时代,村上孩子们 “两国交兵”打泥巴仗,他便是一方的将帅。长大一些,村上的儿童团团长, “罗成队”队长的职位都是他的。在学校里,当少先队干部、班干部、共青团干部等,常常头衔好几个。二是思想积极。特别是政治上革命性强。村里斗争地主恶霸,他跳到台上去打耳光子。1957年反 “右”,学校有两名教师被打成右派,他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批判。1958年 “大跃进”,学校停课上山挖铁矿石,他干劲冲天,还和几个同学一起种了块 “亩产十万斤”的水稻试验田。1965年我国南方邻国战局紧张,他报名参了军。

 凌河之恋(孙玉新)
凌河之恋(孙玉新)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
如果,真的有如果(辛秀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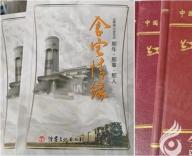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孙仲兴主编的两部文集被多家图书馆收藏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献给五一的歌(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格律诗五首(李辅志) 我的故乡(孙国春)
我的故乡(孙国春)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望春(外三首)(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
飞檐冰挂(李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