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树
文/尤来顺(辽宁喀左)
有树的地方,不一定有人家;有人家的地方,则一定有树。在老人的眼里,这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树可高可矮,可粗可细,可弯可直,只要是生长在自家的周围,便如自家的物件一样亲近了。我们的老房子处在“山沟沟”里,周围有很多的树。有的是自己栽种的,有的是野生的,同样吸取着日月精华,同样感受过风吹雨打,在岁月的不断前行中,它们看老了我的父母,也将自己孵化成一段段传说。
印象里,古代达官贵族、文人墨客偏爱花草,布衣百姓、绿林好汉钟情树木。这似乎与周边的生活环境很有关系。久而久之,花草便带上了娇气,树木则带上了土气。我生长于农村,自是从小就喜欢那些一身“土气”的树木。杨树,榆树,槐树,杏树,桃树,梨树,枣树,等等,它们好似遗传了先祖的相貌,遍布在我家的房前屋后。用绳把狗、牛拴在杨树上,爬上榆树去掏鸟窝,吃槐树花做馅包的包子或饺子,和小伙伴玩藏猫猫躲在杏花或梨花丛中,等等,我都经历过。母亲把院内的两棵树拴上绳子晾晒洗过的衣物,父亲将干枯的榆树皮放在碾盘上碾碎,做饸饹(北方一种面食)时用它当辅料,爷爷则躲在一棵大树下边饮着大碗茶边哼着二人转……这些我也都见过。而那些树木也好似很享受这些与人为伴的过往经历,各自尽情地生长繁殖。记得有一次,我见到母亲晾晒衣物的绳子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了树干里,便对母亲说道:这两棵树会不会死掉啊?母亲轻轻地刮了下我的小鼻子,说:不会的,它们是很顽强的。说罢,母亲还是把绳子解下来,换到另外两棵树上。几天过后,我看见原先那两棵树上留下的伤疤已经完全愈合了。
在故乡,杨树算是众多“土气”树木中的白马王子,容易成活,身材笔直,长得也快,适合盖房子做家具。早些年老家还流传着一种习俗,就是刚刚成家的男女要在院外的一侧栽上两棵杨树,以备自己百年之后做棺木用。我老家的院子外就曾经有两棵参天大树,那是父亲当年亲手栽下的,前些年因为叔叔家要盖房子,急需栋梁之才,父亲只好将它们锯倒了……
老家的槐树多是野生的,木质坚硬,密度大,长得缓慢,浑身长满了刺,因此也叫“刺槐”,适合做农具,比如镐头把儿、铁锹把儿、木犁杖等等。刺槐的花可食用,每年的五月份正是槐花飘香的季节,将其采下,用水一焯,加拌各种佐料便可做成馅,味道香甜中略带苦涩,那是故乡很多中老年人的深切记忆。如今在农家院里,仍可依稀见到它的身影。对了,刺槐还有一个表亲叫国槐,长在很多城市的道路旁,它也开花,但不适合食用,倒是常常可以当做药物来服用,中药饮片里有一味唤作“槐花”的便是也,治疗痔疮很有效。榆树,多是不成大材的,但乡亲们多不去限制它的生长,原因是它的繁殖能力很旺盛,根系很发达。老家山多,房屋多建在山腰或山坳里,榆树也就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物种,对房前屋后的土块固定及水源保护很有裨益。榆钱儿可做榆钱儿饭,榆木可做菜板儿,很耐用。
柳树算是“血统”比较高贵的一个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或是“一丝杨柳千丝恨,三分春色二分休”,似乎皆在表明柳树的与众不同。但它和桑树一样,都不适合生长在各家庭院的周围。这与人们的生活习俗或许有关。
能够开花的树,天生就有一种优越感,毕竟它们的花朵没有温室里的花娇气,耐看,还结果。待杏子、李子、桃子、梨、枣等挂满枝头后,欢歌笑语便混合着果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椿树早些年很常见,常被唤作“臭椿”,如今已不多见,大概与它的体味有关系。樱桃树倒是很讨小孩子的喜爱,每家都有一两棵。
各种各样的树木,植根于故乡的土地上,与人为伴,不管时间与时空如何变幻,都不轻易消亡。这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信仰。就像我们渐渐老去的父母,尽管头发已经花白,但仍然守护在故乡,守望着我们。因为故乡的土地啊,就是他们的根,亦是我们的根。
哦,那些遥远的老家的树啊……
小链接尤来顺,常用笔名:尤中文、布里亚特、来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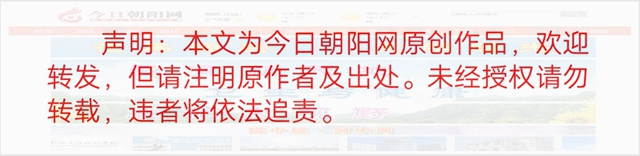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家有贤夫(杨秀兰)
家有贤夫(杨秀兰) 人生是一场修行(晏春华)
人生是一场修行(晏春华) 在阅读中遇见最美的自己(晏春华)
在阅读中遇见最美的自己(晏春华) 考场外的守护(唐士超)
考场外的守护(唐士超) 挖野菜(李文静)
挖野菜(李文静) 瓢虫之死(孙玲玲)
瓢虫之死(孙玲玲) 母亲的菜园(李文静)
母亲的菜园(李文静) 民间故事丨意外(王庆民)
民间故事丨意外(王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