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儿时的大戏台
文/文化信使 李文静(辽宁朝阳)
“春脖子短”,这是常挂在北方人嘴边上的一句话。可不是,春播下种后才一场透雨,天热得就像架起了干柴在烤,夏天说来就来。青苗和杂草较着劲地“蹭蹭”长,辛苦的农人起早薅苗,贪晚锄地,顶着日头追肥……直至把田垄趟上,地里的农活才总算告一段落。
闲下来才看到花都红了,水也绿了,树荫更浓了。软软的风里隐隐有锣鼓声响:“唱戏啦!镇上唱大戏啦!”这消息像长了翅膀的家雀,扑楞楞地落在了每家每户的窗台上。
“想看出戏去呢,也有点空儿了。”母亲给弟弟喂着饭,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
“那就去!我给你们找车,你不早就说要去看他姨了吗?”父亲的语气倒是很痛快。
说去就去,马路上来来往往,找个捎脚的车很容易。翻过山梁,远远地看见,镇子上的大烟囱冒着白烟,那烟囱下面就是大戏台了吧……
悠悠岁月。恍惚间,这是我五六岁还是七八岁时候的事呢?我记不清了。但是,真真切切,我记得童年时镇上那个大戏台——红墙褐瓦、四角高翘的模样。那戏台坐北朝南,背靠铁路,面对市场。雕梁画栋,像年画上的楼阁,又像水乡里的亭榭,自带着些缥缈的仙气。戏台前额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戏台上也是红红绿绿地动:一会是小姐丫鬟游园赏春,一会又是才子书生流落街头,咿咿呀呀听不大懂,只是板胡吱吱扭扭地拉,锣鼓热热闹闹地敲。
更热闹的是戏台下。四邻八乡的人们潮水般涌来,挤在戏台前的大多是本街的老人,坐着蒲团或者四条腿的小板凳;后面的就只好围着站了,里里外外的两三层;也有的嫌热,远远地躲在树荫下,或者趴在墙头上看。人群外是一长溜儿的小摊,有“滋滋”响的炸油条,有高声叫卖的豆腐脑,有五颜六色的大气球,也有香气飘得很远的吊炉烧……小孩子们大多喜欢在卖瓜子糖块的摊子前穿来绕去,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大戏台的幕布后,总觉得那儿会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下一个出来的啥样儿,惦记着爬上去看个究竟。
可是我最终也没能爬上去看看,母亲总怕我跑丢了,看得紧。中午在附近的姨妈家吃了口饭,还没和表哥表姐玩熟识,戏台上锣鼓又响,赶紧跑过来看。一心只惦记着看看《报花名》《刘巧儿》之类广播里听过的评剧,可是等了许久也没有出场。被太阳晒得冒油,缠着母亲吃了5分钱一根的冰棍,甜得心满意足,也算是没什么遗憾了。
不久红日西斜,霞光如醉。戏台上的人物仿佛镶上了金边,竟越发生动起来。悠扬哀婉的板胡或急或缓,如泣如诉,每一弦都像是拉在心上。可是母亲却要带着我们回家了,说弟弟吵闹得厉害,也怕太晚找不到捎脚的车。表哥们拽着胳膊不让走,母亲又说明日得上山给谷子掸虫子,农活可不敢耽搁了。
总而言之,是不得不回家了。好在母亲又说回家会给我们烙油饼,于是又高兴盼望着,心情愉悦起来。
往事如梦。此后,也许又去看过几回戏,却全都记不真切了。自从家里买了黑白电视,连母亲也对去镇上看戏失了兴致。初夏闲暇时,邻居家欢快的迪斯科白天夜里地唱着,似乎也不大听得到锣鼓响了。
二十多年前,我赶火车经过镇上,远远地见老戏台兀自立在市场北侧,很是落寞的样子。戏台柱子上的朱漆大多剥落,几块断砖横亘在台子上,似乎将要被厚厚的灰尘湮没。老戏台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早寻不见昔日的辉煌了。
又是几年,市场大集搬迁到镇子西头,不久戏台也被悄悄地拆掉。眼见着那里起了一幢又一幢漂亮的高楼,车来人往,却再也没人知道,这里曾经有一座热热闹闹的大戏台。
沧桑人世。社会发展得太快了,承载着童年期盼和快乐的大戏台终究还是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消失在了世事变迁中,甚至没留下残垣断瓦让人追忆,如今家乡的文化广场也能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那热闹劲甚至胜过当年。当年围坐在戏台前的老人们早已耄耋甚而作古,往事成风;曾经嘻哈打闹的小孩子也已长大成人,渐渐成了人生戏台上的主角,演绎着属于自己的人生大戏。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卧床多年,每日与电视为伴,还是最爱看戏曲频道,仿佛只有那锣鼓家什“隆咚锵”地响,才会让她暂时忘记病痛的侵扰,忘记晚年的孤独。一日见她盯着屏幕出神,轻轻问她还记得年轻时带我们去看戏吧,老太太瞧瞧我,笑了:“记得,那时候你们还小,那时候日子还穷,可那时候的戏可真好看!”
是啊,的确再也没有看过小时候那样好看的戏了呢!
小链接李文静,辽宁朝阳人。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中学高级教师,文学爱好者。喜爱读书、旅游,闲暇时喜欢用文字抒发心情,记录过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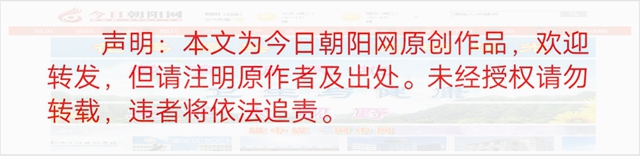
[编辑 雅贤 编审 春语]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生日(孙仲兴)
生日(孙仲兴)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初“烤”九天(晏春华)
初“烤”九天(晏春华)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