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苦是别离
文/文化信使 李法明(辽宁喀左)
我曾经告诉自己要为大伯写点什么,却是一直没能动笔,一是工作有点忙碌,二是总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点。今天我终于写下了这个让我不敢忘怀的题目:人生最苦是离别。
大伯和老爸是一个爷爷的孙子,他们这辈哥四个姐四个,只是老叔和我家大伯早就离开了故乡到了朝阳和盘锦去生活,于是那个叫后稠沟的地方就剩下大伯和我的老爸老哥俩了。
原来的日子过得紧吧,但是有庄稼人的快乐。春种秋收的互相帮忙,盖房子搭屋的总是能先伸手,遇到为难招窄的,张嘴借钱过坎的总是最亲近的人,似乎日子就是这样过来了。
忘不了在村里赶大车的大伯,在送粪的时候让我们也坐在车上,听着他哼着小曲,看着他甩着大鞭子,指挥着那个驾辕的白马,行走在平台地那条平直的大道上。有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也会搞个小把戏,把车套的铁棍藏起来,大伯总是能猜到是谁干的藏在哪里,而他总是乐呵呵的,很少熊我们。
忘不了大伯家杀年猪的时候,大人们在忙活着收拾年猪,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门前的空地里争抢着沾满泥土的足球,满头大汗地玩得不亦乐乎。记得有一年下着小清雪,十几岁的大哥背着六七岁的我到大伯家吃杀猪菜。今年过年的时候,大哥还提起了这件事,只是眼前的大哥今年已五十岁了。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来了,转眼间已经是三十多年了吧。
大概是1990年,大爷爷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当时我还是小学六年级吧,正是吃粮不管事的时候。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吧,上台村当医生的黄家大伯对别人说:抬头纹开了,这老爷子看来是熬不过去了。我也不懂什么,只是觉得大爷爷喘出来的气有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当门外的木匠把大爷爷棺材做好了不久,大爷爷就咽气了。人们说:这老爷子就等着把“房子”做好了才放心啊。
到了我大学毕业,我家也搬离了老家,到县城开始新的生活,于是老家就剩下大伯一家了。大哥二哥在大爷爷离开后不久就相继娶妻生子,大伯也完成了给儿子娶媳妇的人生任务。只是土里刨食的日子不好过,一年忙到头也没啥余钱儿。那时候外出打工经常有欠工资的,大哥二哥也就过着听天由命的日子,不太紧吧也绝对是不太宽裕。后来大哥的钢筋工工钱也涨了,二哥的电工技术过人也成了带工的。哥俩的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了,大伯也就活得更乐呵了。大哥把分家的老屋推倒了,到三里外的老丈人家去住。二哥盖了新的北京平,宽敞的觉得有点空。每年逢年过节的,热热闹闹的,只是家族里两代人喝酒都没啥量,喝两盅就满脸通红。
再后来,没考上大学的侄子有了对象,结婚了,侄媳妇先后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大伯当上了太爷。大侄女考上了本科大学,去年刚刚毕业在沈阳找到了工作单位,开始了她新的一段奋斗历程。大伯也关心自家孩子的婚事,只是大侄女还没完成她爷爷的愿望。
那年腊月二十一,我和老爸照例回老家祭祖,老哥两个见面了也是问寒问暖的,大伯说:知道你们今天回来,你大嫂子准备年糕豆包去了,我都去东边看两回了。曾经的壮小伙,如今也是头发斑白了,关节炎有点让他不再健步如飞。我们都劝他说:也不缺钱,下年就少种点儿地,当个营生吧。大伯也准备把远处的地给大哥种,就留门前的三亩地,权当是锻炼身体了。
正月初三的时候,我们爷几个照例回老家送年,大伯因为肌肉拉伤有点行走不便。我觉得很诧异,大伯的体格除了不算严重的关节炎那是棒棒的,挑十桶八桶水也没啥问题啊,也没多想。当送年的时候,大伯还在祖宗的牌位前磕了头,叨咕着每年说的话:送老祖宗回去过日子,互相照应着走。
正月初五的上午,老爸打电话来说大伯去市里的医院了,下半身没了知觉,在沈阳的二哥和在盘锦的大姐相约去了朝阳。只是初六中午我们等来了更不好的消息,遵照医嘱:大伯这病是急性脊髓炎,坏死的脊髓不可能治好,回家吧,估计这老爷子熬不过今夜。于是在正月初六的下午,拉着大伯的救护车踏着2016年新春第一场大雪,护送大伯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后稠沟。
这年老爸六十六岁,他谢绝了亲朋好友的庆贺,独自一个人到河湾的庙里烧上几柱香,吃了两顿素食,算是完成了他的一个愿望吧。当听到大伯病重的消息,老爸的耳朵一下子就听不见了,打电话就是基本白搭了。当接他的车还要忙活着置办白布、丧盆什么的,耳朵听不见的老爸一下子就急了,拽着我问:咋还买这个了,不是没啥事吗?然后就是泪流满面了。
当我们又一次见到大伯,他静静地躺在火炕上,脖子以下已经没了知觉,只是头脑清醒一点儿也不糊涂。大姐夫说:这就是他的命了,这病有钱也治不了,发展的太快了,一天的功夫就只剩下头脑明白了,可惜了这老爷子这个厚道人啊。
老家左邻右舍的都来了,屋里有点拥挤。老爸贴近了大伯的脸,大伯流着泪说:这回怕是完了,这胳膊大腿的都不听使唤了。老爸啥也没说就是一个劲儿地哭,大哥他们忙着把老爸拉开,老爸却不肯离开,望着他的大哥,满脸地不舍。
前半夜,大伯不停地说话,叮嘱大嫂要好好照看家里的牛,对儿媳妇好点,两个孙子养活大不容易。大伯过一段时间就张罗着喝水,不要雪碧那种甜水,就要家里的井水,每当喝到井水的时候他总是说:“还是家里的井水好啊,凉哇的,哎,我要离开后稠沟了。”听了让人心里酸酸的……
我半夜时候迷糊了一阵子,一点多我又守在跟前。心脏不好的大姐一直在给大伯按摩,按摩那没了知觉的腿和脚,指甲修了又修,只是满手的老茧,让人想起这位老父亲的不容易。大伯对大娘说:这回我是啥也不管了,以后啊,你就指着儿女和侄子吧。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死得明白啊。说得守在一旁的二哥红着眼圈儿去了门外抽烟。
第二天因为单位有工作我必须离开,连说带劝把老爸也拽走了,让永金叔的车把他拉回了家。可是过了不到三个小时,从盘锦赶回来的老叔老姑开车到了街里,老爸又跟着回去了,我们也只好让老姑他们照看着他,别让他太激动。
初七,电话里的情况就是还清醒,也认识人。想见的亲戚能来的都来了,大伯还都知道,和他们说几句话。大约是临近黄昏了吧,大伯说自己的舌头不好使了,估计离要走不远了。在他的要求下,亲戚们给他穿上了最后的衣裳。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大伯还有意识,直到最后离开。
大伯的“房子”是最好的,小村子的老少爷们随车送他最后一程。二哥说:我爸这一辈子,不烦人。就是病来得太急了,也没花啥钱,也没劳累人,不痛不痒的也没遭啥罪,到老还是不肯麻烦人啊。大伯在梨树坡子的祖坟地安了新家,守候着他熟悉的村子,还是听着他喜欢听的评戏?
人走了,最后的程序就是送盘缠。95岁的姑爷爷依旧是给离开的人写了一份路引,也算是西去的路条通行证吧。老学究写的东西没有标点符号,断句也考究人的文化水平,大伯的路引是培玉大爷爷给念的,他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觉得我也一定会念,但是我不敢保证我不哭。
大伯走了,大娘还在那曾经的老屋里,过着怀念的日子。大伯的头七我们没能回去,五七的时候我估计也回不去,因为村里换届,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想如果三七没有特殊事情,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的,毕竟大伯是我们在老家最大的牵挂啊。
我想用这样的对联总结大伯的一生。上联是:勤俭持家五十年,下联是:忠厚为人一辈子,横批是:音容永在。我不知道这够不够精炼,但是我觉得大伯做到了这几个字,他的一辈子,没有大起大落,但是他用他的一生告诉晚生后辈做人的道理。
断断续续写了两个小时,忍不住的泪水让我几次停下来,我不知道远在天堂的大伯是不是知道,我们在想他……我也不知道,大伯对我这段文字是否满意?
小链接李法明,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1975年生人。在辽宁省喀左县五个乡镇辗转打拼二十年,现供职于喀左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喜欢读书,爱好旅游,闲时弄花草,静处赋文章。偶有文字见于报端,愿以文会友,短长互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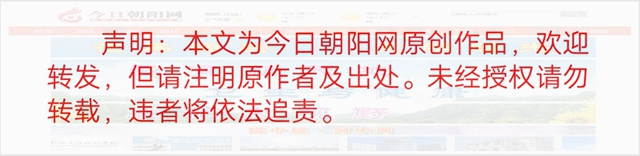
[助编 秋水 责编 雅贤]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我和著名作家浩然的交往(胡相生)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花开的声音(张艳彬)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宁飞) 生日(孙仲兴)
生日(孙仲兴)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怀念坚强善良的妈妈(胡相生)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由《种树郭橐驼传》想到的(谢晓丰) 初“烤”九天(晏春华)
初“烤”九天(晏春华)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
你永远铭刻在我记忆的石壁上(谢晓丰)